- 吴晓波:中国人是如何轻贱商人的
- www.3puok.com 2010-08-11 11:45:28
-
“中国从来就有轻商的传统”,这似乎已成公论。时至今日,这一“公论”似乎似乎要重新思考,在我看来,古往今来,中国轻视的是商人,而从来不轻视商业。
说到轻视商人,倒真是罄竹难书的。早在管仲那时候——公元前七世纪,他给百姓分等级,是为“士农工商”,商排在最后,经商是末业。到了汉朝的刘邦,他最讨厌商人,专门颁布诏书,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,不得乘坐华丽的车骑,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,以表示困辱——“天下已平,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,重租税以困辱之。”他还规定,商人不得从政,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不行,所谓“禁锢不得为吏”。当时朝廷没有钱,就推出一个 “纳粟拜爵”的制度,平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。可夸张的是,就是在“卖官”的时候,朝廷竟也规定,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。
这种对商人极端蔑视的政策,在后来的历朝历代稍有缓解,但是从根本上却没有改变。广州商铺出租
可是,为什么又说中国从来不轻视商业呢?
,由此类推,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。表面上,国家并没征税,实际是“无不服籍者。” 因为实行了盐铁专营,齐国迅速成为当时最强的诸侯国,齐桓公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,管仲也留下了“千古一相”的名号。从那时起,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为国家经营。这种统治艺术冠绝全球。与欧洲列国相比,那里的治国者从来只知道从税收中获得收入,在中世纪,一些国家真的穷到没有办法了,连一根烟囱也要征税,结果弄得天怒人怨,他们没有想到,其实只要把煤炭专营起来,每一斤煤多加一点钱,远远比征烟囱税更能增加收入。只有中国,想到了从国营工商业中直接取得利益。所以,一些有见识的史家便提出,中国的治国者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“工商富国”的一拨人。 接下来的问题是,为什么一方面知道“农不如工,工不如商”——这是司马迁先生在《货殖列传》中的原话,可为什么另一方面又要拼了命地压抑和蔑视商人呢? 道理在于:当国家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,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,后者自然就应该遭到打压。所以,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,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。这种颇似矛盾,实则一体的观念会造成怎样的景象呢?下面一段故事,在历史上一再发生—— 汉朝初建之时,国力极度赢弱,皇帝要出巡,居然配不齐四匹肤色一样的骏马,而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,穷窘得只好乘坐牛车。国贫民穷之际,朝廷一改管制政策,“开关梁,弛山泽之禁,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,交易之物莫不通,得其所欲。”经过七十年的“文景之治”,出现前所未见的盛世,“民则人给家足,都鄙禀庾皆满,而府库余货财”。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,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。与此同时,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。司马迁的《史记中》记载了二十一位当时的富豪,个个都神采飞扬。可是到了景帝的儿子汉武帝时期,再度实行管制政策,盐铁等重要产业重新收归国有化,所有盐商、铁商、流通商、金融商几乎全部一一破产。 让人叹息的是,这样的景象在此后的两千年里一再地重演。我们这个国家,只要没有外患内乱,放纵民间,允许自由从商,三十年可出现盛广州商铺出租
还是从两千多年前的管仲说起。他主政齐国时,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,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回国家专营。当时其他的诸侯国,征税靠都是农业税,可是只有管仲看到了一个事实:工商业——煮盐冶铁——所能产生的利润远远的大于耕地种田。在农耕时期,这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,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。更重要的是,这是唯一的工商合营产业,其原料得自天然,有垄断经营的优势,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,一面自行贩售,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展转变化,繁殖累积,其财势不可阻挡。
更要紧的是,国家直接控制工商业,老百姓并不觉得受到了损失。管仲就举例说,大凡一个农户,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,都需要针、刀、耒、耜、铫、锯、锥、凿等等铁制工具,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,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,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,由此类推,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。表面上,国家并没征税,实际是“无不服籍者。”
因为实行了盐铁专营,齐国迅速成为当时最强的诸侯国,齐桓公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,管仲也留下了“千古一相”的名号。从那时起,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为国家经营。这种统治艺术冠绝全球。与欧洲列国相比,那里的治国者从来只知道从税收中获得收入,在中世纪,一些国家真的穷到没有办法了,连一根烟囱也要征税,结果弄得天怒人怨,他们没有想到,其实只要把煤炭专营起来,每一斤煤多加一点钱,远远比征烟囱税更能增加收入。只有中国,想到了从国营工商业中直接取得利益。所以,一些有见识的史家便提出,中国的治国者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“工商富国”的一拨人。
接下来的问题是,为什么一方面知道“农不如工,工不如商”——这是司马迁先生在《货殖列传》中的原话,可为什么另一方面又要拼了命地压抑和蔑视商人呢?
道理在于:当国家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,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,后者自然就应该遭到打压。所以,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,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。广州商铺出租
世,五十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,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,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,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。 历代史书中的所谓“大帝”,从秦始皇、汉武帝、成吉思汗到康熙、乾隆,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实践者,在其统治期内,商人阶层从来就是被打压的族群。这些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,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,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。具有迷惑性的是,他们在口头上都以“均贫富”——救济贫困,抑制豪强——为号召,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“天然”的仇恨,而实际上,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,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。所以,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。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,因为要与民争利,所以又必定多为严厉的酷吏,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,然后又私下作法敲诈,结成权贵资本集团。 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,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。而最具有讽刺性的是,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,大多用于国防军备,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。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,国强易得,民富难求。中国对“商”的态度是如此的混乱和矛盾,说到根子上,都是制度惹的祸。
这种颇似矛盾,实则一体的观念会造成怎样的景象呢?下面一段故事,在历史上一再发生——
汉朝初建之时,国力极度赢弱,皇帝要出巡,居然配不齐四匹肤色一样的骏马,而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,穷窘得只好乘坐牛车。国贫民穷之际,朝廷一改管制政策,“开关梁,弛山泽之禁,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,交易之物莫不通,得其所欲。”经过七十年的“文景之治”,出现前所未见的盛世,“民则人给家足,都鄙禀庾皆满,而府库余货财”。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,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。与此同时,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。司马迁的《史记中》记载了二十一位当时的富豪,个个都神采飞扬。可是到了景帝的儿子汉武帝时期,再度实行管制政策,盐铁等重要产业重新收归国有化,所有盐商、铁商、流通商、金融商几乎全部一一破产。
让人叹息的是,这样的景象在此后的两千年里一再地重演。我们这个国家,只要没有外患内乱,放纵民间,允许自由从商,三十年可出现盛世,五十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,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,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,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。
历代史书中的所谓“大帝”,从秦始皇、汉武帝、成吉思汗到康熙、乾隆,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实践者,在其统治期内,商人阶层从来就是被打压的族群。这些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,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,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。具有迷惑性的是,他们在口头上都以“均贫富”——救济贫困,抑制豪强——为号召,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“天然”的仇恨,而实际上,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,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。所以,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。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,因为要与民争利,所以又必定多为严厉的酷吏,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,然后又私下作法敲诈,结成权贵资本集团。
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,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。而最具有讽刺性的是,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,大多用于国防军备,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。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,国强易得,民富难求。
中国对“商”的态度是如此的混乱和矛盾,说到根子上,都是制度惹的祸。
世,五十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,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,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,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。 历代史书中的所谓“大帝”,从秦始皇、汉武帝、成吉思汗到康熙、乾隆,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实践者,在其统治期内,商人阶层从来就是被打压的族群。这些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,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,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。具有迷惑性的是,他们在口头上都以“均贫富”——救济贫困,抑制豪强——为号召,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“天然”的仇恨,而实际上,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,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。所以,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。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,因为要与民争利,所以又必定多为严厉的酷吏,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,然后又私下作法敲诈,结成权贵资本集团。 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,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。而最具有讽刺性的是,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,大多用于国防军备,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。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,国强易得,民富难求。中国对“商”的态度是如此的混乱和矛盾,说到根子上,都是制度惹的祸。广州商铺出租
★延伸阅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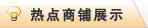
- 最新商铺新闻






